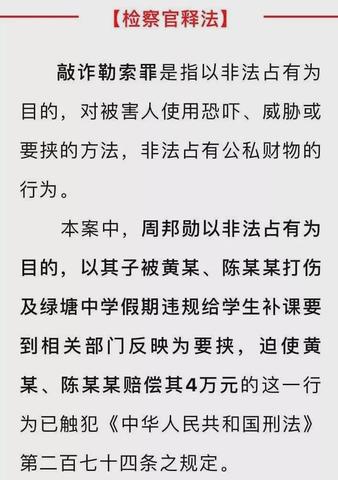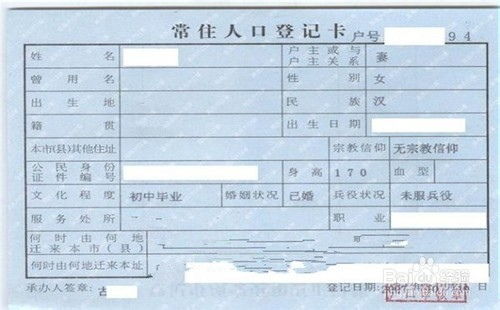法律讲堂文史版 法律讲堂文史版张程
子曰
汇聚智慧思想,传递深度观点。对话名人名家,听他们说……
嘉宾:李山
李山,师从著名学者启功教授、聂石樵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在《诗经》研究、先秦两汉文字研究领域卓有成就。2016年4月受邀到武汉讲学,凤凰湖北根据演讲内容及问答整理以下访谈实录:
讲学就像“姜太公钓鱼“。
您曾通过《百家讲坛》的平台向观众进行学术的“普及”,您认为在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要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又如何看待大众的反馈?
一个电视节目有它的收视率。据我了解,《百家讲坛》的点击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收视率不是很好,因为它的播出时间有问题,而且大家都忙。现在很多80后、90后从网上吸取知识,网络上应该有这些东西。但这还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兴趣的自来,没兴趣就是你跪下给他讲,他也不会来。
对于观众的反馈,我是碰到了就听听,但从来不上网去看,因为网络上什么话都有,不看更省心,省事不如省心,不听、不看、不争辩。有的时候一些观众来信,我会回答。比如读者来信问为什么“大(dà)夫”这个词念“大(dài)夫”,还有几位观众来信说“二千石”的“石”应该读成“dàn”,而不是“shí”。对此,我都会回信告诉这些朋友我的理由。因为他寄信给我了,作为礼貌,是应该有回复的。
我是称不上“大师”的老师。
您是如何走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之路的?人们对您的恩师启功教授评价往往为“大师”,您认为“大师”又应该是怎样的?
我当年高考时曾填了两个志愿,一个是财经,另一个是师范,最终被一所师范大学录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再到博士一直都在师范院校。我从一开始就没讨厌过当老师,尤其是读高中时遇到了一位特别好的语文老师,让我暗下决心希望将来成为和老师一样的人。最初步入教师的行业是在大学刚毕业时,那时仅靠56块半的工资维持着每个月的生活。然而也是在真正做了老师后,才发现教师其实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能把读书、教书、偶尔再写一点书这么几件事结合起来。而正是这种职业的吸引力牢牢地控制了我。
展开全文
老师这种职业貌似平凡,其实要做好特别不容易。基本的修养和对工作的认真只是最低标准。我实际上把教师当作了我的生活,骨子里就比较喜欢,对我来说我没有感觉到它是外在的,无论好与不好,就是一种真实的状态。
我觉得首先一个大师必须在学术上有一批重要的著作,这些著作为学术树立一种典范,这种典范影响了一批人,也造就了一批人。北师大老校长陈援庵说,一个人死后五十年,还有人印他的书,这个人就差不多是一个大家了。
年龄虽然是大师的一个因素,尤其像人文科学需要时间的沉淀,德高望重,但不是一个必然限制。但比如像朱生豪,活了三十多岁,却翻译了莎士比亚。还有很多人40岁就去世了,但留下了一大批著作。而且这些人学术成果的取得,不是到了八十岁,而基本上是在它们五六十岁——生命的顶峰就达到了,他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活得长才成了大师。卓著的学术成果,广泛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这是应该是大师的一个标准。
文学的眼光去看历史。
您作为一个文学专业而非历史专业的老师,在面向大众讲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是如何寻找侧重点的?

需要明确的是,先秦、两汉,即上古这一段时期,本身就是 “文史不分家”的情况。而且文、史的学科分类有时候是为了方便,不必把它们分得那么清。一个历史人物,用一种文学的眼光去看待他,你可能会更理解他的处境。
比如说秦惠文王这个人,他的父亲秦孝公任用了商鞅十八年之久,史学家在记录商鞅变法的时候,对这一期间的很多史实谈都不谈,而只是讲变法本身。但在这期间,时为太子的秦惠文王犯了错误,商鞅收拾了他,当然实际收拾的是他的师和傅,最后太子掌权,自然杀死了商鞅。
秦惠文王心里有愧,曾经到华山求山神原谅———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些玉板,这些玉板上面就写着他生了病以后,向华山山神的乞求。他说:“我得病可能有两条原因,一是对山神祭祀不周,但这是因为西周灭亡,礼乐崩坏,不是我故意的;二是有一个人行法律,被杀了,但这不是我干的。”行法律被杀的人就是商鞅。像这些地方你说是历史还是文学?显然分不清楚。
古人写史、讲史的目的往往是希望后人以史为鉴,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部分历史可以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甚至是科技发展的规律。读史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启发人,就像培根说的“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当然受过文学思维的训练,我们在写一本书,讲一次话时,就要注重启发性,要注意细节性的东西,而不是单单说出一种大的规则。
写历史必须顺着说,今天发生了什么,明天发生了什么,但有时候历史可以反过来想,上升到精神层面,文学和历史也就不再分得那么清楚了。对于历史人物,很多历史的记载、文献的记录都充满了各种想象和不实之辞,所以我们只有深入了解历史人物,让他“活”起来,才能对他产生一种理解,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启发意义。
比如像蔺相如这个人,现在戏曲里都是由须生唱的,很文雅,然而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的人。我们都学过《完璧归赵》那一段,蔺相如对着秦昭王,把这块璧攥到手里,靠着墙,要挟秦王。蔺相如这个人极聪明,他跟秦王打交道,几次都是以小命对大命,心想自己反正是贱命一条,就看秦王你能不能豁得出来。所以他不是我们后来的老生演员所表现出来的很文雅的形象,尽管他有很高的文士气,但仍带有铁、铜的色彩。
博学是一种境界,追求但不敢自居。
您的学生对您的评价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有“博学”、“犀利”、“激情”,甚至“豪放”。您如何评价自己?
还是比较准确的,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博学是我的追求,我在努力,但绝不敢自居。从启功老先生身上才能看到真正的渊博,那是一种境界。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做学问)较真儿,敬业就是和平年代的节操。
我不是一个很条理化的人,而且很容易紧张,所以特别不擅长参加比赛。因此包括讲课我也不太习惯受形式的约束,基本属于想与讲同时进行的自然状态,这也许正是学生们上我的课时总觉得神思遐飞、“一走神儿就被甩出十万八千里”的原因吧。
传播知识其实也是在反思知识,尤其是文化史这门课,它有一种内在的东西,特别能激起社会责任感。其实教师就是在通过读书和教书这种方式来承担我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是我的职业,因为我喜欢我的职业,始终就让我觉得它好,好为人师啊!

京剧是一种熏陶,我们玩得很认真。
您在业余生活中,有哪些爱好?
京戏可以说是我自己平时唯一的娱乐。说就像你们迷恋流行歌曲一般,一旦会唱了,累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喊上两句,调整调整心态便可“高高兴兴回家去,家家扶得醉人归”。如果每周二晚上,你从北师大主楼7层文学院办公室前经过时,千万不要诧异听到了京胡声和几个京戏迷扯开嗓子在唱京戏,那就是我们。
我们玩得很认真的。原来我嗓子只能唱到降E调,现在都能唱到E调了。有一次我去台湾开会途经深圳,晚上到广场散步时老远听到一阵京胡声,循声找过去竟然发现拉胡的老汉竟然是读大学时在安徽认识的朋友。18年不见的戏友,相逢在异地却还是因为那片京胡声,这种缘分也因京剧而变得妙不可言。
凤凰网湖北频道出品 本期策划/编辑:王爽婧
与本文知识相关的文章: